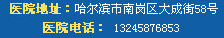凡是在农村或者小县城生活过的人看《树先生》都会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似乎每个村头都有这么一个傻子,他们无所事事,到处游荡,被人调笑。总是笑着的傻子背后有多少辛酸?他们又是怎么变成傻子的?周围人即便知道一些也并不真正关心,他们的亲人也只是觉得丢人。这就是《树先生》,导演用黑色幽默和诗意的镜头语言为我们讲述这么一个大家都见过的傻子的身前身后事,然后在这个讲述过程中加入导演对周围世界的冷静观察和忧郁思考。
灰暗的天空,灰暗的街道,灰暗的房屋,灰暗的农村。一个修车的男人,从狭窄黑暗的修车地沟里爬了出来。树,是他的名字。在影片当中,王宝强被省略了姓氏名字,只有“树”的简称。他家门口有棵树,那里发生过一起意外惨剧。在这里,树又变成了痛苦的阴影,一旦事件发生,它就生根发芽,破土而出,挥之不去。越到后面,观众则会发现,影片涉及了高度现实的拆迁用地题材,树先生发了神经,死活不肯离去,他与那个即将消失毁灭的村庄捆绑在一起。他的一生,好像跟那片土地无法分离,合为了一体。
树先生是一个善良而可怜的小人物。因为尽管每个人心中都认为自己有一天可以做成大事,但其实大多数时候你只能蹲坐在一个角落里看周遭变化,悲哀的是你一直尽全力假装自己其实有能力跟得上,直到自己再也撑不下去。他有心仪的女孩子,会谈恋爱,像每个人一样,在恋爱时文思泉涌,才艺爆发,能写下触动人心底的短信段子。而就这么短短一个多小时的影片之间,这个不知名的卑微小人物本有着还算正常轨迹的人生,怎么忽然就会变成最后那个傻笑着走在田埂上疯癫了的的树先生。
每个人小人物都有难以启齿的生活困境,每个平凡的人都会面对生活中的种种挫折和挑战,树先生也不例外。树一直求而不得的,与其说是面子,不如说是自尊,彻底没了自尊的树,终于失去了做人的资格。树先生努力想进入主流社会,却始终游离于主流之外,他的疯癫更像是本我的自主选择,只有疯掉他才能真正清醒,才能实现像弗洛伊德所说的“压制的隐秘愿望与伪装起来的自我满足”。
这是一部超现实主义电影,所谓的超现实并不仅是“二手玫瑰”那几句充满隐喻和二人转趣味的歌词,而是树先生独树一帜的生活方式和职业、家庭发展轨迹。从一个无人理睬的助理修车工,到一个资本家们都点头哈腰的半仙,树先生完成了一次华丽丽的成功转型。偶像与实力同在,草根与精英并存。电影上去就给人一种灰色的感觉,非常地压抑,一遍看完,甚至分不清哪些是“树”的幻想,哪些是真正的现实。不过,说实话,那种小人物的悲哀,完全贯穿了电影始终;同为小人物,总有一股气憋闷着,想要说出来才会感觉好一点。
整部电影的叙事于落后、凋敝、满目疮痍的九十年代乡村缓缓展开,这部作品在贾科长的监制下,呈现出冷峻粗粝的现实感,却又如莫言将诡谲气息泼洒于凋敝的乡土之中,甚至带着一点点库斯图里卡的荒诞意味。这种荒诞与现实的糅杂契合了树一步步崩溃的精神世界。这部电影几乎浓缩了这30年中国乡土社会变迁的缩影。它的观后感受可以类比文学的乡土变革代表人物陈忠实、贾平凹、莫言、余华、刘震云的作品大集。
在真实里,我们文明的活着,而几多人没有好好去实现想做的事,被亲人、朋友、老板、事业、房子或下一代所束缚,并将此无奈薪火相传给别人或后代,直至全世界出家。这部影片从两个方面展现出社会的病态,一方面靠毁坏他人利益使自己富裕起来的人,另一方面是想实现自己但被这个病态的社会所残害,树先生就是典型的代表,真实的描写了很多人的无耐特别是最下层的农民残害的更狠。
每一个村里的疯子,都是树先生的翻版。他做不好事情,说不好话,看着呆,但他并非傻,他觉得这样活着没意思,但也不知道该去哪里寻找自己的尊严。他们也想活出自己,但种种因素困扰着他们,让他们无法实现自己,他们只能寄托在神灵上,通过神灵来惩罚那些靠不光明的手段富了之后欺负那些不如他的人。
很多人说这部《树先生》是中国版的《小丑》,是当今文艺片下的“重口味”。其实在《Hello!树先生》里,从远处的篝火开始,真实和虚构的界线就在不停转换。当韩杰远离了山西的故土,他却依然选择了广袤的农村土地。他貌似不关心故事的精确度,只关心效果,注重经验界限之外的狂喜,像慢慢着火的屋子,像血红色的天空。不管真实或虚构的段落,从幻想到逃离,树先生都太自我了,拥有着精神的超脱,这是电影人物最重要的气质。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wdmm.com/zcmbyf/1257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