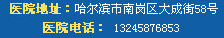不经意间,春就慢慢走远了。
记忆中的春,是早上出门偶然瞥见的两朵小黄花,是刷新朋友圈一眼带过的花花绿绿,是考试结束才注意到的一片粉红,是挽臂逛街抬眼看到的白色花球,是回家路上远远注视的半路姹紫嫣红。
冬去春来、春去夏来、夏去秋来、秋去冬来,本都是自然现象,中国古代诗人将自身情感投射其中,一处景、一件物……于自然现象外,逐渐成为寄托古今中国人万千情感的“意象”。
春是怎样的意象?或者说它寄托着怎样的情感?
初春是憧憬与希望。
立春一过,实际上城市里还没什么春天的迹象,但是风真的就不一样了,它好像在一夜间变得温润潮湿起来上,这样的风一吹过来,我就可想哭了,我知道我是自己被自己给感动了。
暮春是落寞与失望。
每年的春天一来,实际上也不意味着什么,但我总觉得要有什么大事发生似的,我的心里总是蠢蠢微动,可等春天整个都过去了,根本什么也设发生……我就很失望,好像错过了什么似的。
看《立春》时,脑海中依次浮现出“时代性”“追求梦想”“生不逢时”“天赋+不幸”等短语,但看完演职工作人员的滚屏字幕,脑海中却浮现了“社会环境中个体的独特性能否保留”“个人独特性在社会环境中将走向何处”等长句。
第一个问题是社会环境中个体的独特性能否保留。
电影中有两个人物较为独特,一个是梦想走上巴黎歌剧院的大龄未婚乡镇中学音乐老师王彩玲,一个是教妇女扭秧歌、跳广场舞的大龄未婚男芭蕾舞老师胡金泉,社会对他们的评价中分别是不正常和不正经。
面对这种社会环境他们是如何做的呢?
王彩玲领养女儿做屠户,胡金泉强奸未遂判入狱。
看似磨灭了个性,活成了别人眼中的样子,实际上在他们心中,独特的个性永远不会被磨灭。
有两个保留个性的细节我非常喜欢。
王彩玲带女儿做唇腭裂手术,偶遇了曾经追求她并被她拒绝的周瑜,对方问“你什么时候结婚的?”,她一句话没回,抱着女儿扭头就走。我要为她这个举动鼓掌叫好,因为看似为家人、为生活、为生存不得不低头的王彩玲,其实一直在高昂着头,她依旧热爱歌唱、依旧梦想着有生之年能够站上巴黎歌剧院的舞台,把《慕春》唱给更多人听。
胡金泉把女学员带到男厕所,假装强硬地对其实施性侵,之后在众多女学员的注视下面带微笑、昂首挺胸地走回训练场地,装入磁带、打开收音机,在周围漆黑、场地昏黄的灯光下立起脚尖、优雅起舞。面对前来探监的王彩玲,胡金泉说“我在里面挺好的,我这根鱼刺,终于从那些人的嗓子里拔出来了。我踏实了,大家也踏实了,实际上,我挺高兴的。”似乎是觉得话语力量还不够,他穿着布鞋在王彩玲面前立脚尖旋转。
我为这句话、这个动作落泪了,一直在我眼中柔柔弱弱的胡金泉,以拔掉嗓子里的鱼刺譬喻和监狱里也可以跳芭蕾的举动,不仅显现出了他异于常人的“强壮”,也让我这个局外人看清楚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我既不是拥有鸿鹄之志的王彩玲也不是甘愿坐实谣言胡金泉,我是担心朋友成功考上美院的周瑜,我是把苦水倒给自认不如我的小张老师,我是没有个性也看不惯他人个性的普罗大众。
但人并非生来就没有个性,就像世界上没有完全相同的一片树叶一样,我们每个人生来都是独特的,但在社会环境中却逐渐向三个方向转变——个体主动或被动融入群体,个人与群体走向对立、个体改变群体认知。
前两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比较常见,即普罗大众与少数群体,最后一种情况出现的几率较小,但只要出现就会成为社会舆论的焦点,例如“清华毕业养猪”“硕士农民”“大学毕业回家养狗”等等。
有良知的媒体或者说主流媒体会把这些极少出现的个例当作独特个体,通过报道他们与众不同的人生选择,鼓励更多人坚持自己的个性,追求自己的梦想,改变身边人的固有观念。
向最后一种方向转变是很难的,我们多少人能扛得住别人的流言蜚语,又有多少人能把流言蜚语转变为哑口无言,亦或是交口称赞。
至少在现在的中国,这样的人依旧是“新闻”,依旧是社会舆论的焦点,改革开放初期与改革开放后四十年,改天换地与一成不变其实是同时存在的。
正所谓:立春之后,寒意尚存。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wdmm.com/zcmbyf/130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