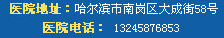露天电影(-03-:19:45)现在的孩子已经不知道什么叫露天电影了,而我是看着露天电影长大的。说这话的口气有点像掉了牙的老祖母,但看露天电影的确是二三十年前的事了。我七岁之前的时光都是在乡下老家度过的,那是离城二十多公里的偏僻小镇,虽然偏僻,戏园子却有一处,虽然那戏园子简陋得只有青砖搭起的舞台。戏园子里唱没唱过戏我不知道,但电影的确是演过的,那个时候的电影也无非是《沙家浜》《红灯记》《地道战》之类吧,但我对这样的电影没有丝毫的印象。记忆里的第一部影片是《闪闪的红星》,潘冬子有一张苹果似的圆脸,电影插曲《小小竹排江中游》的旋律至今也还难忘。有年冬天,说要演《大闹天宫》,传的一个镇里的人都知道了。戏园子里的长条凳、短板凳、竹椅子、小马扎上午就摆了个满满当当,天还没黑,人们就从四面八方朝戏园子里涌去,那架势真比赶年集还热闹。我一心想看孙猴子是怎么大闹天宫的,激动得连晚饭都没吃就扯着妈妈往戏园子里赶。天黑了,哒哒的放映机响了,下面是一片欢腾。但银幕上却不是孙猴子,而是扎着白羊肚手巾的人在砸石头,山西农民砸完石头是鞍钢工人炼钢铁,而后是石油工人钻井。不断有人在抱怨,也不断有人在鼓劲,说《大闹天宫》在东庄上演着呢,已经有人去拿胶片了。但我却撑不住了,当不知哪里的纺织女工来来往往接线头的时候,我的上眼皮和下眼皮也终于接到了一起,趴在妈妈肩头睡着了。第二天,当人家说起孙猴子的筋斗云时,我气得哇哇大哭。耗时间看了那么多的纪录片,却到底没看上孙猴子怎么和玉皇大帝斗法。七岁那年我到城里上小学。那时我家住在牡丹北路,离家很近的双河路上就有一家露天影院,那里可是天天晚上都演电影,因为城里人无所谓农忙农闲。晚上吃过饭,只要肯花两毛钱买票,就能看上场电影。影院里的座位都是石头做的,一长排一长排的石凳逐层地高上去,看起来颇为壮观。但冬天坐在石凳上看电影,又是露天影院,一场电影看下来,整个人都冻木了。那时我大哥也就是十八九岁的年纪,每月挣三十块钱的工资。他是个电影迷,大半的工资都换成了一张张的电影票。《黑三角》《冰山上的来客》《阿诗玛》《丫丫》《舞台姐妹》《简爱》《佐罗》《追捕》,都是我跟着他从露天影院里看来的好电影。还有一部电影叫《王子复仇记》,也就是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什么幽灵、什么老国王新国王,罗里吧嗦的,不知道他们在说些什么。想问问一旁的大哥,他正看得专注,黑暗里盯住荧幕的眼睛都在放光,却一句也懒得给我解释。上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我家从牡丹路搬到了青年路,离家不远就有家电影院,这家影院不是露天影院,票价比露天影院贵了一半。而大哥也谈起了恋爱,他还是经常去看电影,只是带的是他的女朋友而不是我了。不知道双河路上的露天电影院是什么时候拆掉的,偶尔从那里经过,会想起坐在石凳上看电影的少年时光。现在的影院很豪华很气派,但大部分的时间是空着的,因为看电影的人少了。我仍然喜欢看电影,有时候去影院,有时候窝在家里看街上淘来的碟片,沉浸在光影里的时光是格外幸福的。作者简介:辛云霞:媒体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有散文集《女人笔记》出版。转自辛云霞博客平台壹点号青未了菏泽创作基地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wdmm.com/zcmbzz/13843.html
沈阳白癜风医院 http://www.bdfyy999.com/辛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