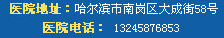年奥斯卡颁奖礼上,《蜂蜜之地》在所提名的最佳国际影片和最佳纪录长片两个奖项上分别输给了在奥斯卡上斩获4项大奖的《寄生虫》和获得年美国独立精神奖最佳纪录片奖的《美国工厂》。对于这个结果,大多数人并不感到意外,毕竟《蜂蜜之地》相比前两者来说,鲜为人知。影片讲述了作为欧洲大陆最后一个女采蜂人,64年出生的喀迪丝与年迈半盲的母亲居住在马其顿一处荒凉的农村中,贫穷和疾病伴随了她的半生。她翻山越岭在悬崖间找寻野生蜂巢,带回家附近的人造岩洞内耐心等待蜂蜜的成熟,等到收获的季节,她依循古老民族的养蜂传统,严格地恪守着“取一半,留一半”的准则,她长久维系着自然的微妙平衡,也总是能因此得到丰厚甘美的自然馈赠。等到把蜂蜜过滤装罐,她会穿上淡黄的长裙,裹束起蓬松的头发,带去镇上的集市换取刚好够照料她和母亲两人的钱和日用品。如果这部纪录片仅仅只是如此,恐怕不会获得世界电影单元纪录片作品的陪审团最高奖,一户游牧家庭的到来,为该片注入了亮眼的戏剧冲突:一心想要赚更多钱,不愿恪守传统的“取一半,留一半”的准则,这户游牧家庭不顾喀迪丝的劝阻,肆意采收着蜂蜜,甚至连河道上树干里最后的蜂巢也不放过。粗壮的树干可以支撑人在上面走动,却阻挡不了电锯的砍伐。他们养的蜜蜂同时也害死了喀迪丝岩洞里的蜜蜂,两家人也因此产生了争执。游牧家庭想要赚更多钱,喀迪丝却失去了生计来源。整部影片由此突然有了剧情线、有了张力、成为一个完整的故事,情感上更加丰富饱满。影片中喀迪丝和游牧家庭,代表了这世界完全不同的两类人。前者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她会毫无保留地教邻居养蜂取蜜,帮乌龟翻爬障碍,抚摸猫咪吟唱歌谣,用树叶救起落水的小蜜蜂,和邻居的孩子一起收听音乐,唱歌荡秋千,像个大姐姐一样和他们相处,一起爱抚初生的牛犊,给孩子吃最好的蜜巢……而后者则代表贪婪和利己主义,轰鸣的发动机和聒噪的牢骚吐露出他们在利益下的嘴脸,蜜蜂的生死与他们无关,他用贪婪的姿态,向大自然擢取着更多的资源,毫无原则和章法。他的一意孤行最终招来大自然的报复,而当他面对“躺枪的”受害者喀迪丝时却没有任何担当,他的妻子甚至用孩子来起誓,撒谎脱罪,失了最后的底线。除了人与自然,影片中还有着关于家庭的拿捏也非常细腻动情。昏暗的的房间里,喀迪丝半盲年迈的母亲安安静静地躺在窗口边的一张小床上,只有当她口渴或者吃东西的时候,才会出现在镜头里,若不起身,就是一片沉沉的隐秘。面对病重的母亲,她从不抱怨,忙碌一天夜色漫来,一盏煤油灯下就是她和母亲的喃喃世界。当地一年一度的赫迪尔莱兹节前,哈提兹打开从镇上买来的染发膏要给自己染发。母亲缓慢地问道:“是不是很需要我帮你?”“可惜,我能帮忙的时日子早过去了。”“太难了……”没法反驳的喀迪丝拉了拉老母亲,故意要老母亲帮忙系头上的毛巾,她要让母亲感觉到,即便是此刻,她也可以帮到女儿!母亲动情地说:“女儿,你要平安健康,让我吻你一下吧。”喀迪丝答道:“让我也吻你一下。”当影片渐入尾声,这一年的寒夜格外冰冷,邻居种下的恶果,让喀迪丝失去了她所有的蜜蜂,也失去了她的母亲。那个唯一给她带来安慰、带来关心的人,给她带来麻烦、同时又帮她驱走寂寞的人,永远地离开了。她独自坐在空床上,只能把那些说给母亲听的话呢喃给猫咪。而至于游牧家族,面对收货商的威逼利诱,他违背了原则,不听劝阻把所有的蜜都取来卖掉,最后他的牛死了五十只,只能再次狼狈的流浪。人们责怪家族的男人暴劣、贪婪和自私,但你是否注意到了他的犹豫和无奈。正如他面对商贩时低头说的那句,“为了孩子”。《蜂蜜之地》全片犹如一首烛光下安静的诗作,从头至尾没有一句旁白,没有一段采访,这份完美的恬静叙事源自摄制组3年小时的素材储备。而这样一部看似鸿篇巨制的「史诗」,背后团队却只有5人:2位导演、2名摄影师、1位剪辑师。影片中,蜜蜂成为贯穿全片的线索,镜头下喀迪丝养蜂的“一半给我,一半给你”,无意间也与联合国倡导的世界环境议题不谋而合:一半关于自然,一半关于社会。如何平衡这架命运的天秤,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深思的问题。这一世界性焦点议题,《蜂蜜之地》的导演将其具象化为在这片土地上,养蜂人对细微生命随处可见的关怀。虽然大自然的报复也殃及到了善良守则的养蜂人,但这也正是导演在这真实人间下参悟出的哲学:人生,本就是酸甜苦辣交织尝尽,蜂蜜之地,也并不尽是甘甜。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wdmm.com/zcmbhl/14004.html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wdmm.com/zcmbhl/14004.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