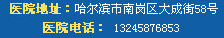“艺术”这个词很容易和“阳春白雪”联系到一起,但这世界上总有许多人梦想成为什么画家、文学家、音乐家……有很多人说《立春》是追求艺术的“文艺青年”们的挽歌。
艺术其实没有那么神秘,它带给我们的是一点精神上的享受,然而总有人想要用它去改善自己的生活,突破现处的社会地位,以为亲近艺术就能让自己看到不同的世界。
事实往往并非如此,艺术是纯粹而美丽的,扎根泥土之中又高悬天空之上,它或许真的能为你带来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身外之物,为你带来世人崇拜的眼光,但更多时候,它就仅仅是一场供人缅怀的美梦,一朵盛开在灵魂里的花。
小城里的文艺青年
黄四宝热爱油画,刚出场就躲在床下,被自己老妈骂得狗血淋头,连续考了多次美院都名落孙山,他自己也说自己没那么高境界,好不容易找到愿意给他当人体模特的女人,他却因隔壁欢好之声而心烦意乱。
他的种种表现,都说明了他并非是真的追求艺术,从作画水平到创作精神,他都十分业余。
王彩铃去歌剧院面试,自以为天赋秉异的她哀求对方听自己唱一曲,她的歌声惊艳了电影观众,却没能惊艳面试者,预想中被录用的画面并没有出现,别人只是淡淡说了句:“行了,知道你水平了。”
大概只有胡老师艺术造诣最高,芭蕾一跳就是十几年,他对艺术爱得纯粹,从未想过要站上什么世界性的大舞台,他只是单纯地想要起舞,也并不对自己舞蹈老师的职位感到不满。
偏僻封闭的小城里,三人对艺术都有各自的追求,他们都算那个时代的“文艺青年”,也同样不为人理解,有才不售,活得颓丧郁闷。
从艺术幻梦中醒来
黄四宝是才学最浅陋的那个,也是觉醒最快的那个,去了一趟深圳,见识了大城市的繁华,深刻体会一番“市场经济”后,他便恬不知耻地回乡开起婚姻介绍所,专宰大龄未婚男女的钱。
在大马路上与故人黄彩玲相遇也未能激起他半分曾经对艺术的向往,他不但选择了平庸的生活,还跌得更加彻底,靠坑蒙拐骗营生。
王彩铃最悲惨,好在她最终从幻梦中醒来,一步步接受残酷的现实,她征婚未果后领养了一个小女孩儿,这位拥有歌剧梦的音乐老师改行卖起了羊肉,找偏方治疗脸上的黑斑痤疮,开始脚踏实地的生活。
她曾因为上天赋予的美妙的歌喉而自命不凡,不甘于像小镇其他人那样庸碌的生活,她觉得自己应该站在巴黎歌剧院里唱歌,一曲完毕,台下掌声雷动。
她曾说:“我一贫如洗,又不好看,老天爷就给了我一副好嗓子,除了这,我是个废物。”
她认为老天爷夺去了她拥有美丽容貌的可能(脸上的黑斑暗疮),才为她另开一扇窗,赐给她一副好嗓子,因此她一直不愿意主动去治疗自己的脸,害怕失去唱歌的天赋。
但她对艺术的追求是十分功利的,她只是想要借这种才能赢得众人的尊重,因此才安耐不住虚荣地撒谎说:“人民歌剧院在办调动手续,我很快就去北京了。”
她其实已经凭借才能在小镇谋得了不错的职位与社会地位,若仅是热爱歌剧,王彩玲完全可以安安心心当老师,将这份热爱传授给学生,利用业余时间发挥余热,沉浸于歌剧带来的精神享受
但她却希望歌剧为她带来梦想中的功名利禄,当这样的目标无法实现时,她哀叹命运不公,自己怀才不遇,但最后王彩玲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宿命,她把理想定得太高太远,以至于荒废现实生活,青春岁月已一去不返。
三人里,最单纯澄澈的大概是胡老师,他的一生仿佛都是为跳舞而生,可以毫不腻味地跳上十几年,为了能不被人诟病,专心跳舞,他甚至跑去跪求王彩玲和他假结婚。
为反抗男人们投来的歧视目光,他轻薄学员,落得个坐牢的结局,他终于证明了自的“男性”气概,可以无忧无虑地跳舞,但也因此失去了自由。
影片中最让人敬佩感动的莫过于王彩玲去看胡老师那场戏,他穿着打理得齐整洁净的囚服,喜滋滋地告诉她,监狱里的布鞋也能立脚尖,他仍然可以享受艺术带给他最纯粹的快乐。
胡老师与王彩玲的不同之处就在于,他忠于自己的内心,对外界如何能否欣赏认同芭蕾不大在意,他只是不可避免地被流言蜚语纠缠,让自己母亲跟着蒙羞,所以才采用这种决绝地方式与世俗决裂,获得超脱。
艺术不同于艺术家
三人命运虽然看着相似,但各自的精神追求却有云泥之别,艺术并不等同于艺术家,艺术之美存在于每个平常的细节中,那些富有生命力的生活日常,那些平凡人的朴实善良难道不美吗?
年少多情的我们,痴迷于优秀的文艺作品,向往着艺术家们的生活,但在仔细思索之后,还是选择以平淡安稳的方式度过一生,而那些百折不回在追寻艺术的道路上走下去的人,少数成功了,大多数却撞得头破血流。
当你摒弃功利性和优越感时,你才能透过艺术的窗口,开辟出一片明净美妙的精神世界,那是比金钱地位更值得追求的事物。
转载请注明地址:http://www.qwdmm.com/zcmbzl/13004.html